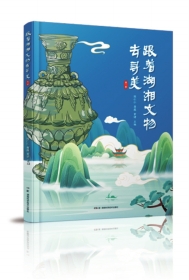文物作向导湖湘学子寻美家乡
——“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”征文优秀作品展
2025年9月6日
2025年6月,由潇湘晨报十几岁杂志社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图书《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》(第一册)上市,这本集齐湖南大学岳麓书院、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、湖南博物院6位专家、学者,专为10至16岁青少年写作的“大家小书”,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湖湘传统、湖湘文化、湖湘美的历程。 暑假期间,由潇湘晨报十几岁杂志社发起的以“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”为主题的征文活动,共收到小初高各学段学生来稿逾两百篇。他们写《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》一书带来的新视角与新发现,写他们与文物之间的亲近与对视,写对家乡更深一步的了解…… 综合专家评选意见和晨视频“i教育”频道发起的“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·暑期共读成果网络票选活动”投票结果,我们选出十篇作品,分两期进行刊发。 正如《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》主编陈仁仁所说:“要想有一种审美的自觉,是需要我们费些功夫努力去寻求的。这也是我们把这本书提名为‘寻美’的原因所在。” 寻美湖湘,是一场持续的行动,我们始终在路上。 古人向美的纯粹之心铸就永恒 王筱玥(长沙市博才云时代小学六年级2002班学生)指导老师:陈石勇张昂波 《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》从陶瓷器、玉石、漆器、服饰四个方面,勾勒出湖南文物的绚丽画卷。 陶瓷器由泥土经复杂工序制成,从实用的陶器到观赏的瓷器,体现了人类从生存需求到创造追求的跨越;玉石被视为石之美者,从实用石器发展为装饰与礼器,象征礼节、德行与精神寄托;漆器历史悠久,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以红黑对比、云纹为主,展现楚人奔放热烈的气质;服饰自黄帝时代起,从遮体衣物演变为身份象征与美的追求,承载着华夏礼仪与章服文化。 书中介绍的文物,或精致细腻,或古朴粗犷,但无一不是当时极为珍贵的艺术珍品。蛋壳陶仅有0.2毫米的厚度,曲裾素纱单衣仅重48克……看到这些,我不禁心生疑问: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物质环境下,工匠们究竟是如何创造出如此惊艳的艺术品的呢? 或许是古人心中怀揣着对永恒的追求,又或许是古人那份一心向美的纯粹之心,铸就了这般惊艳无数后人的成就。 一本指导我逛博物馆的书 文:成果(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青石学校2003班)指导老师:谭娟金竹馨 《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》的服饰篇,让我认识了西汉的“时尚女神”——辛追夫人。那件仅重48克的素纱单衣,“薄如蝉翼,轻若烟云”——我反复品味着这八个字,脑海中一位身着单衣的女子款款而来,衣袂飘飘,如梦如幻。 当我来到湖南博物院的展柜前,我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。那件素纱单衣就静静地躺在那里,它不仅是一件衣服,更是汉代织造技术的巅峰,是古人对美的极致追求。“巧夺天工”一下子就在我脑海中具象化了。 “文物不是冰冷的器物,它们有温度、有故事、有生命。每一件文物背后,都站着一个时代,都藏着无数人的喜怒哀乐。”《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》中的这句话,成了我参观博物馆的密钥。从此,再逛博物馆时,我不再走马观花,而是认真了解每一件文物,想象它们承载的社会生活与文明密码。 看似普通的简牍,绝不普通 文:陈滢嘉(长沙市弘益高级中学2401班)指导老师:李伟 “北有西安兵马俑,南有里耶秦简。”走进里耶秦简博物馆,这句话便映入眼帘。我在心中打了个问号,为何它能与兵马俑并论? 当我的脚步循着时间的辙痕,从秦瓦的纹路,走向帝国宫阙的恢弘构想,最终,停驻在里耶秦简面前,我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。 里耶秦简博物馆两个镇馆之宝——“九九乘法口诀表”木牍和“迁陵以邮行洞庭”简牍,它们让我看到了一个“鲜活”的秦朝。 不过,我差点错过这一精彩的发现,因为这些简牍看上去实在普通,它们只是静卧在幽暗的玻璃展柜里,一束昏黄的光温柔地笼罩其上。乍看,还以为就是几片残缺、发黑、边缘甚至有些毛糙的木片,像刚从哪个老屋房梁上拆下来的旧物。 经讲解员提醒,我才知道,里耶秦简“九九乘法口诀表”木牍是目前世界发现最早、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,证实我国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九九乘法口诀,比西方早六百多年。“迁陵以邮行洞庭”简牍则被称为“中国最早信封”,让今天的人们得以窥探秦朝完善、高效的邮传系统。 文物提供了一条穿越时空的路径,让我更好地理解古人与他们生活的社会。 与一万多年前的陶片打个照面 文:杨未雨(永州市道县玉潭东阳学校2301班)指导老师:姚雪琴宋灏漭 《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》介绍了我国制陶的历史,最早可追溯到距今18000~17000年,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的陶片就是证据。 玉蟾岩,位于我的家乡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附近。据说,这里出土的陶片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发现的陶片都要早好几千年。早在旧石器时代,先民便在这里繁衍生息,并发明了陶器的烧制方法。我仿佛看到,我们的祖先把湿泥巴捏了又捏,用火把它烧成能装东西的容器。 书中介绍,正是原始农业的出现,增强了先民对泥土特性的了解,进而发现水与泥的关联。“小颗粒的粮食变为食物,需经火的烹煮,耐火炊具便至关重要,陶器也就应运而生。”读到这,我理解了道县“天下陶本”美誉背后的文明进程。 合上书,我想起了玉蟾岩更多让人激动的事。在玉蟾岩遗址,考古学家还发现了1.2万年前人工栽培水稻的种子,这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古代碳化稻粒。 家乡的文明史如此源远流长,我的内心骄傲极了。 衡州窑工铸就的时空胶囊 文:廖章俊(衡阳市第八中学609班)指导老师:旷晓辉 沿着湘江支流耒水溯游而上,三十里河岸散落着星罗棋布的古窑址。云集窑的龙窑遗迹蜿蜒如卧龙,窑壁经年累月形成的琉璃质釉斑,在斜阳里闪烁着孔雀蓝的微光。衡州窑工是真正的时光旅人,他们以耒阳高岭土为纸,以松柴火焰为笔,写就了半部中国民窑史。 衡州窑工取湘中素土为骨,汲蒸水清流为魂。其器形之妙,在“三分佛性,七分烟火”。衡州古窑的器物总带着地道的湖湘脾性。衡州窑的青釉盘口瓶,颈部的莲瓣纹似从洞庭湖的涟漪中采撷而来;衡山窑的瓜棱执壶,流线型的壶嘴仿佛湘江转了个温柔的弯。最妙是那些民间日用器皿,茶盏底足残留的茶垢,酒壶腹部的握痕,都在无声诉说着市井烟火的温度。 在云集窑遗址出土的瓷枕上,我发现了独特的“文字纹”。窑工们将“福”“寿”等吉语刻成印章,在素胎上捺出质朴的文字。这种将书法与制瓷完美融合的智慧,恰如屈原《离骚》中“内美修能”的注脚——既重器物之用,更重精神之养。 这些沉睡的瓷片从来不是冰冷的文物,它们承载着衡州窑工的心血,也传递着过去的审美印记。